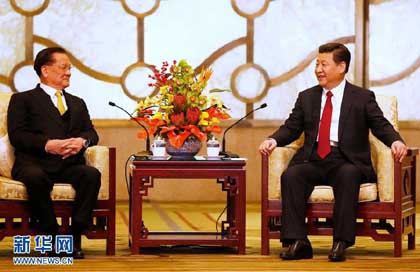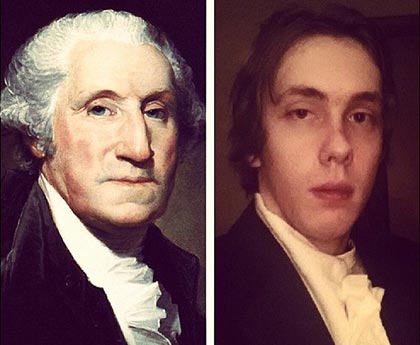为了在北京买一套房,37岁的小伙儿钱建新,称自己不敢多挣钱,不能过得富裕,连媳妇都不敢找。
不过,至今也没人能说清,他幻想中的那套房子,正矗立在北京哪一块金贵的土地上。或者,连影儿都没有。唯一确定的是,他盼了差不多5年,额头上添了几道抬头纹,硬茬茬的一窝头发里,又伸出几根白头发。“奔四”的他,仍然是个晃来晃去的单身汉。
但他还是个有“希望”的人。这个跟着他晃荡了5年的希望,就是那套房子——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建设的“保障房”。可等了5年,他连一次“摇号”的机会也没盼来。
如今,坐在路边一家暖气不足的面馆里,回想起2008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他的笑意,从额头上的一道皱纹,滑到他微微上扬的嘴角,停顿下来。他说,那个热气腾腾的“希望”,正是从那年的夏天开始孕育,“那会儿北京奥运会还没开始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模仿当年居委会大姐跟他说话的口气,钱建新升了一个语调,“上头的文件来了。”按照此规定,32岁的钱建新有资格申请“经适房”(“保障房”的一种类型),“简直太幸运了”。
幸运的钱建新填好“经适房”申请表,反复将那几页纸抻得平平整整,再放进写字台抽屉里。随后,他看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专门到他家里来“调查情况”,觉得心里头的希望变得更“踏实”了。
2009年1月26日,这个日子从钱建新嘴里脱口而出。这天,他正式成为北京市朝阳区“保障房”轮候者之一。被幸福感包裹的钱建新,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到常营乡的一片保障房小区看了看。虽然,当时东五环外的常营,周边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但钱建新已经开始在心里勾勒家的蓝图。他指着其中一栋新楼房,对自己说:“将来的家就在这儿啦!”
在他眼里,希望就像一个打满了气的氢气球一样,不断地膨胀,飞到天上去了。随着希望攀升的,还有北京的房价。2009年,北京大部分新售楼盘都是“日光”。房价几乎一天一个样,颇流行的段子是,“出去买了一个包子,回来时房价又涨了一千”。
拿到申购资格,钱建新就像一块“香饽饽”,亲戚朋友恨不得“蹬破”他家门槛,给他张罗对象。婚恋市场里,房子几乎已成默认的“加分项”。钱建新是未来的有房一族,一片前景光明的样子。
但是,钱建新不敢接受人家的美意,因为一旦他找个媳妇,收入超过1200元,他的申购条件就会“超标”,无异于选择“自动淘汰”。
不光不能谈婚论嫁,多挣钱也不行,除非不想等保障房了。钱建新在一家社区文化公司工作,月薪2000元左右。每到年底,领导喜气洋洋地要给他涨工资,钱建新就像避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
“这真是一个悖论啊。”钱建新一直盼望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脱离父母,成家立业。但是为了这套房子,他又和自己最初的梦想,背道而驰。
好在等房子的头两年,希望还是充盈的。那时,每到全国“两会”时,“保障房”就成热门议题。与此同时,在各大新闻网站诸如“今年‘两会’你有何期待”的调查中,“调控房价”通常是柱状图里那个高出一大截儿的选项。
钱建新收集了一些报纸,上面印着“今年大概有2500多套“经适房”房源进入配售阶段”之类的报道。这些官方的表态和醒目的数字,曾经让钱建新的希望变得更具体。就这样,左等一年,右等一年,钱建新搁在抽屉里的报纸,开始变脆、发黄。连同它们一起褪色的,还有他的希望。
2011年,钱建新开始不淡定了。他起初给自己一个“两年”的期限,“觉得那时房子差不多能‘到手’”。但他仍在“轮候中”。此时,北京的房价趋势也有些飘忽不定,实行买房“限购”政策。
那时,钱建新看过朝阳区东五环外的一个小区,“复式的小户型,特价卖1万多元一平方米”。这或许是出生在工人家庭的钱建新,考虑买商品房的一次好机会,虽然这个小区距离垃圾场不过2公里,楼面上空两三分钟就飞过一架飞机。可最终钱建新还是错过了买一套“哪怕是偏点儿破点儿”的商品房,他一直在等“经适房”。
终于,钱建新坐不住了,每个月去居委会和街道跑一趟,但每次只能听到“不知道”、“等着吧”。
而在北京,除了钱建新,纠结于“等着吧”的保障房轮候家庭,超过10万个。钱建新加入了一个超过300人的QQ群,群成员都是朝阳区经适房的轮候者。他们把自己的“昵称”统一写为“朝阳0901”的样式,阿拉伯数字表示轮候的起始时间。也有不少人,在统一样式之前,加上“等不起”、“无奈”、“花儿都谢了”、“不知道”等前缀。
钱建新每天泡在这个群里,看到这些人在群里讨论的大多是“房姐在北京为何有40多套房子”或者“假离婚,离了再结”等话题。
有时,钱建新觉得这个QQ群就像一个“难民集中营”,大家像“精神病人一样”相互安慰。有人抱怨:“现在想开了,以后有钱就挣,管它超不超,总不能让这破房子把人逼死吧。”但更多人附和着:“苦命啊,还是等吧。”
“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钱建新说。在北京,没有本地户籍的人,连申购保障房的资格都没有。有些人等到房,退出那个“集中营”。他们给仍在“轮候中”的人,“又添了几分希望”。
如今,37岁的钱建新的人生计划表上,仍然没有“结婚”两个字。曾经有姑娘跟他表白,甚至要“以身相许”,但是他称,自己像只乌龟,缩进壳里。他对婚姻,显露出一种超乎常人的“淡然”,这令周围人以为,“他感情受到过伤害”。
钱建新的父亲觉得,儿子为等房子,“还是受到影响”,性格里有了几分压抑。有时在家,钱建新总是“不言语”。这让老钱“很愧疚”,跟儿子掏心窝:“谁让你生在这个家庭呢!”
由于至今没买上房,钱家人活得有些“憋屈”。岁数不小的钱建新还在“啃老”,不仅要“啃”父母那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要“啃”老人家的退休金。平日里,钱建新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只敢进平价的饭馆,和异性吃饭才埋单,男性聚会就“AA”制。
有人嘲笑钱建兴,“太傻了”、“真窝囊”、“不思进取”。他为自己辩白:“是我没能力挣钱吗?挣多了,就‘超标’,被淘汰。就算不等了,房价这么高,就算一个月挣1万元,也买不起啊。”他还说,“有人分到房后,转身就去换了个收入更高的工作”。
钱建新迟迟迈不进“经适房”的大门,和他一起在门外晃悠的,还有大把的时间和青春。
有时,钱建新会安慰自己,他不是“等房”者中最悲催的那个人。他有个异性朋友“小刘”,今年33岁。小刘从4年前年开始“等房”,等成了“大龄剩女”,而且患上了抑郁症。
小刘有时会跟钱建新聊天,吐露心声:“等房子让我绝望了。”她还悲观地说,“昨天看新闻有人跳地铁,我也真想去跳!”
他们都感叹:“为了等这房,生活都扭曲了。人生好像被房子给绑架了。”
被不知在何处的房子“套牢”以后,希望对于钱建新而言,更像是一剂麻醉剂。他恨它,“早知道会等到现在,当初我借钱、卖血、卖肾,也要去买套商品房”。但是,他又需要它,“就像一个糖球一样吊着你”。
从2012年开始,钱建新和其他几个轮候者多次去找朝阳区房管局、住建委,甚至还去北京市信访办投诉,但没有得到让他们满意的答复。最令他们困惑的是,“究竟有多少套保障房房源,如何确定轮候者的摇号资格,又有哪些人住在保障房里”。这些疑问就像北京冬天的雾霾一样。
一眨眼,又是一个夏天,北京房价再次冲上一个高点。钱建新对“房价”已经麻木,他刻意回避跟房子有关的事情。他不爱逛家居店,一看到电视里播装修节目就立马换台。他也从来没有幻想过,未来的家是“北欧风格”还是“地中海风情”。他无奈地说,“等买到保障房,也没有钱装修了”。
“五年了”, 没能等到参加一次摇号的钱建新,终于撑到极限。他说,好像听到“‘砰’地一声,气球胀破了”,希望又蔫回了球皮状。
这一次,钱建新拖着装满75个保障房轮候家庭诉讼材料的拉杆箱,就像拽着所剩无几的希望,走进法院。去年10月,他们将朝阳区政府告上“公堂”,这是北京首例保障房家庭集体起诉政府案,在全国也不多见。
一直被人嘲讽“窝囊”的钱建新,觉得自己像一个“勇士”。这令他身边的不少朋友难以置信,因为在他们眼中,钱建新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话也慢声细语,不像那么“胆大”的人。
75个家庭提起行政诉讼的理由是,“保障房信息不公开”。他们认为,“怕的不是等,而是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最终,他们的起诉被驳回。但是钱建新和代理案子的律师,并不认为“他们败了”。代理案子的律师何峤巍说,“这场诉讼,促成部分保障房轮候家庭和政府的对话,督促政府对保障房信息进一步地公开和透明”。
就在案子开庭前,朝阳区进行过一批“经适房”摇号,但钱建新又不在其中。因为苦等5年,也没等到一次“经适房”摇号,钱建新改为申购价格更高的“两限房”(“保障房”的一种类型),他自以为后者“中奖”的可能性更大。结果,他又错过了,不得不感慨“就像蒙着眼睛,盲目地等啊等啊”。
今年的“情人节”,如果不是碰上“元宵节”,差点又成为一个与钱建新无关的节日。这天上午,北京市两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开始网上申购,瞬时点击量超6万,网站被挤瘫痪。有人说,“这阵势不亚于‘双十一’大抢购”。
头发有些蓬乱的钱建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平静地说:“还要继续等,再给自己两年的期限。”本报记者 陈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