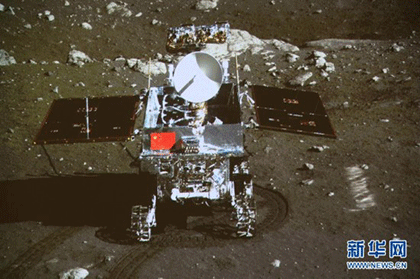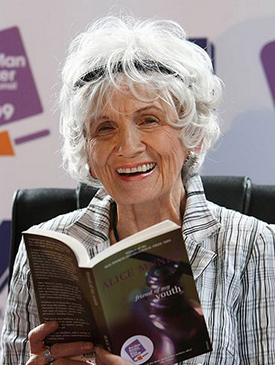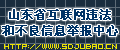首席评论
□潘洪其
昨日报载,针对北京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北京市人大代表李其军提出,北京应当制定“产业负面清单”,禁止低端产业进京。北京市副市长陈刚介绍,北京现在每年新增六七十万人,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了大量人员就业,使城市不堪重负。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特大城市,目前的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和环境资源承载量都接近“极限”。人大代表提出建立“负面清单”制度,限制乃至禁止流动摊贩、个体理发、小废品收购、小商品批发等低端产业进入北京,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缓解人口环境资源和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低端产业直接涉及城市普通居民特别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问题,限制乃至禁止低端产业进京,也就意味着限制乃至禁止大量普通居民和农民工在北京谋生,在此敏感语境下,人大代表的意见立即遭到众多网友和读者的质疑,这样的结果是不奇怪的。
特大城市面临的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在上海、广州、天津、重庆等城市也同样存在。之所以有专业人士一再提出限制低端产业的建议,决策部门及有关职能部门也曾将此提上议事日程,是因为低端产业吸引大量人员就业、助推城市人口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制约大城市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严峻考验。
大量事实证明,当城市发展和扩张超过一定规模,住房、交通、生态环境等问题就会越来越难以解决,并可能形成加速恶化的态势。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早于中国几十年上百年,他们建设和发展大城市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化大城市,在规模人口达到700万—800万以后,就进入缓慢增长甚至停止增长阶段,为城市进一步完善交通、绿化等基础设施,优化管理运行机制留下足够的空间。近年来,北京等大城市虽然加快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建设,并实行汽车限购限行,但交通拥堵状况仍然日趋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加突出,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大城市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战略选择。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两次会议做出的上述部署,明确了以新型城镇化克服“大城市病”的城市发展思路,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科学制定和完善大城市发展规划,提升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发展层次,改进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市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那些聚集大量城市人口、加重城市负荷、妨碍城市格局优化的低端产业,实行限制或禁入措施,推动其转型升级以符合大城市产业发展需要,或倒逼其转移至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镇。
大城市限制、禁止低端产业,不应简单视为对低端产业从业人员的偏见与歧视,而是优化大城市产业结构,改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小城镇之间产业布局的内在要求,是我国大城市健康、成熟发展过程中难免付出的必要代价。在低端产业从大城市迁出转移的同时,还需要将部分教育、医疗卫生、金融、文化娱乐、旅游服务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资源从大城市转移出来,改变大城市公共资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别是中小城镇公共资源严重匮乏的失衡局面,以扩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镇吸引就业的空间,为容纳中低端产业人员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