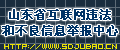《让“死”活下去》陈希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文/李伟长
不知不觉间,史铁生先生离开我们两年了。他生前朋友多,读者也多,怀念文章自然不少。在这些怀念文章中,有一个人的文字尤其值得一提,就是陈希米――史铁生的遗孀。她的新书《让“死”活下去》,悼念亡夫,怀念逝去的岁月,遥寄哀思。
这是一部饱含热泪的长篇情书,一个妻子写给亡夫的情书,有倾诉,有怀念,有哀思,也有思考,句句含情,句句带泪,感人至深。怀念亡人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自西晋潘岳写下悼念亡妻的《悼亡诗三首》后,便成了一种独特文体。唐代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都是名句,至今读来催人泪下。贺铸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更是不着一个悲字,却满篇孤独,相思成灾。当代文学中,巴金的《怀念萧珊》和杨绛写的《我们仨》随笔集,都是名篇,前者怀念亡妻,后者怀念丈夫和女儿,温和的文字藏着命运悲怆。
悼亡文章之所以动人,第一在情深,所谓情深才能意切。但凡感人肺腑的怀念文章,无不记载着夫妻生前的恩爱浓情,即使二人阴阳相隔,那分感情依然温热如初。陈希米自1989年与史铁生结婚,两人结婚时,史铁生已经染重病,靠轮椅行动,后来又靠透析维持生命,每周三次。陈希米悉心照顾了他二十多年,无怨无悔。爱与病痛纠缠相随,二人的爱情是一段佳话。史铁生生前说,没有陈希米,他绝对活不到现在,把陈希米送到史铁生的身边是上帝对他最好的眷顾。他们俩彼此相依、相生和相长,可谓生死相依。从陈希米来说,她不是女佣,不仅仅是一个帮助角色。她照顾史铁生,因为她爱他,这是她深爱的男人。
陈希米对史铁生的情感之深,令人动容。如书中所言,没有谁规定瘫痪的人就不可以有爱情。对陈希米而言,史铁生就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没有史铁生在,生活最可怕的不是眼泪,是沮丧,极度的沮丧,那种尖锐的对活着的沮丧。“每一样东西,每一个时辰,每一点每一滴都在说你不在!到处都是你,到处都没有你。”“现在,不想见任何人。她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她最惦记的,时刻不忘的是他。但她不愿意跟别人说起他,也不想别人提他的名字。”他去世之后,她最大的遭遇是,凡事再也不能问他怎么办!史铁生为死做了很多准备,他要让人家知道,陈希米不仅是他的帮手,也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知己。为此,他还公开了当年写给她的情诗。因为身体的残疾,史铁生的爱,“曾经从来不被承认”,如今那些嘲笑爱情的人终于眼睁睁地看见了爱情的存在。
悼文只渲染感情,是远远不够的,有流于煽情的危险。除了爱,此书还有一层意思值得注意和赞赏,便是作者对生死、爱恋和肉体的思辨。长期陪伴史铁生对抗病痛,加上陈希米自身在神学和哲学方面的修养,使得她开始思考生与死这些哲学问题。书里充满了对生死的逼问和思索,对肉体和精神的思虑。这有别于其他悼念文章,除倾诉哀思外,也在思考死是什么?人死了,怎么办?承认死亡,接受死亡,需要一种仪式吗?从对死的排斥到接受,从无法理解到认识到“死是生命的常态,人必然要经历一个死,一个与自己相关的死”,缓存了许多思想爆点。这对后来者,无论是文学人,还是别的,面对不完整的生命,都有许多启示。
爱人去世,如何继续生活?陈希米说,想念死人就是说你要带着他的死,去活。必须承认他的死,才能活。必须理解他的死,才能活。那种活,不是以死为中心,是以孤独为中心。这就是陈希米内心的全部声音。在滴血般的倾诉式书写之后,在对爱人的死亡经过理性与感性混杂的思索后,陈希米明白了活下去就是“生命热情”之所在,为另一个人活,即使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也要找到一种方式,延续“热情”。写作就是最合适的方式,想象他在场,把做过的事,读过的书,写给他看,读给他听,写出来了就是存在,就是与他在一起的一种方式。
爱一个作家本不容易,做一个瘫痪作家的爱人更不容易,其中冷暖滋味,外人难以体会。在陈希米的笔下,对于自己受过的苦难,受过的委屈,半点不提,足见她对史铁生在乎到何种程度。对这种奉献的唯一解释只有爱,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爱――爱得无私,爱得无微不至,爱得宽容,甚至有些失掉了自我,但这就是爱,没有道理的爱,这和身体是否残疾没有关系。
史铁生是不幸的,遭遇病痛;史铁生也是幸运的,他有陈希米陪在身边。如果说,史铁生的写作是个奇迹,那在这个奇迹里,有一个女人始终陪伴左右,她叫陈希米。我们应该感谢她。